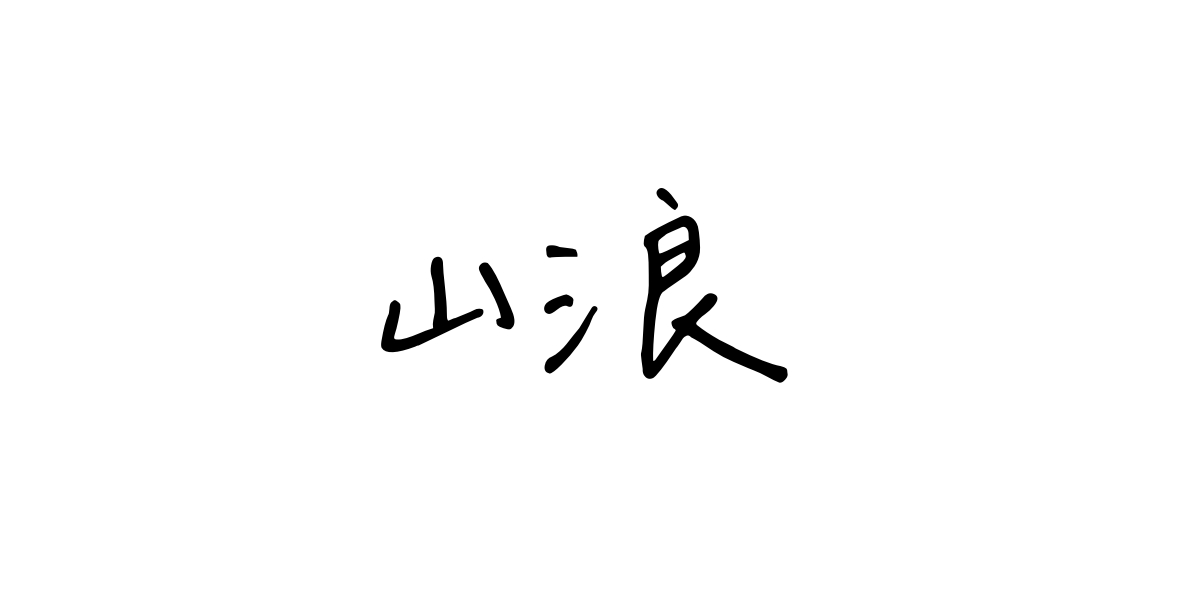三合院,一名滿頭花白的阿嬤聽見我們的招呼聲,慢慢地步出室內。這裡是彰化縣埔鹽鄉的豐澤村,鮮少有超過五層樓的建築,放眼望去盡是綠油油的稻田,幾戶古厝座落其中。我們騎車穿梭於綠野迷宮,一兩戶門前擺有零星的雞毛撢子,但這都不是我的目的地,最終機車在擁有藍色鐵門的三合院前停了下來,庭院長了一座茂盛的雞毛撢子森林,兩側的鐵窗上掛滿了各式雞羽製的半成品,這片閃耀著咖啡色光澤的森林守護者是陳忠露──更是臺灣最後的雞毛撢子職人。
「你們來這邊!」迎面走來的阿嬤許金英正是陳忠露的妻子,她領著我們到鐵棚下的一張摺疊桌旁,只要陳忠露外出期間,碰上散客來訪,一律由她代夫出征,擔任DIY雞毛撢子的指導老師,教學過程也樂於分享自身的故事。
夫妻倆的一生是從何時與雞毛撢子密不可分的?這得回溯到陳忠露的年少時光。
雞毛撢子起緣與姻緣
早期為農業社會,家家戶戶都會養雞鴨鵝,逢年過節或有客人來訪就會現宰來吃,現代高級餐廳提倡的產地直達餐桌,實則遠在1950年代的農村就已蔚為流行。鴨毛和鵝毛具有保暖效果,製作冬衣或棉被時派得上用場;雞毛無法提供人類溫暖,村民殺完雞後,徒留一地的雞毛,任風起舞。廢棄的雞毛成了附近乞丐們的玩物,他們將雞毛拾起來、黏在木棍上嬉戲,一般人見狀只覺得好笑,抑或投以同情眼光;陳忠露的父親倒是從中看見一絲商「雞」,認為拿來清除灰塵似乎很不錯,又近乎無本生意,便到處蒐集雞毛以及竹子,自做自售起雞毛撢子。
那一刻開始,陳忠露的一生,就注定與雞毛撢子牢牢地綑綁在一起。
國中畢業,十六歲的陳忠露沒有繼續升學,不愛念書、一心想賺錢的他,選擇與父親一起製作雞毛撢子,慢工才能出細活,一天產量相當有限,二十來支已達生產上限。當年苦守家業無人問是常態,不像現在只要有噱頭,很容易一PO網就成名天下知。陳家的雞毛撢子靠得全是客人食好道相報,一個傳一個,實實在在的「口碑行銷」,有了知名度,漸漸也有人專程來向他們訂製;陳忠露退伍後,雞毛撢子也來到黃金時代。距離豐澤村車程約三十分鐘的鹿港,是民間信仰的重鎮,至今漫步鹿港老街仍可看見不少傳統工藝,如:佛具店、製香業以及木雕藝術產業等;由於原木只能乾擦,不宜以濕潤的抹布擦拭,雞毛撢子理所當然成為不二的清潔用具。因此年少的陳忠露曾走路至鹿港,向鹿港的佛具店及木雕店銷售雞毛撢子,一段時間後,才改騎著插滿雞毛撢子的腳踏車往返,最遠還曾騎到南投竹山兜售,一支平均售價一塊二到一塊八,最高紀錄則是賣到兩塊三。許金英說,以前的錢比較厚,現在的錢比較薄,沒有賣幾百塊無法維持生計。
雞毛撢子的全盛時期,連夜趕工趕到連吃飯時間都沒有乃陳家常事,訂單曾多到必須雇用二十多位女工來協助,許金英就是當年來幫忙製作雞毛撢子的女工之一,沒想到這一幫就是一輩子,名副其實的「嫁雞隨雞」。雞毛撢子,閩南話發音有祝賀「起家」之意。以前的人準備女兒嫁妝或搬遷的時候一定都會買一支雞毛撢子,也會煮一隻雞來吃,象徵成家立業。
「啊就看對眼了!我的娘家離這裡五分鐘而已。」許金英笑得燦爛,有那麼一瞬間,彷彿窺見嬌俏的少女靈魂。
對於陳忠露夫妻倆來說,的確是踏踏實實靠著雞毛撢子「起家」。

兩人手中的姻緣線不是紅色的,月老賜給他們的是綿延不絕的白色棉線,如同雞毛撢子製作過程中,棉線必須緊緊纏繞著雞毛,兩人透過雞毛撢子相識相戀、進而情纏一甲子的歲月,聯手灌溉這片雞毛撢子盛開的森林。旁人眼裡的雞毛小事,可是夫妻倆堅守一世的志業,五名兒女也在雞群的羽翼下長大成人,現在兒女和媳婦閒暇之餘也會幫忙兩老做個幾支。
一支雞毛撢子的誕生
一開始雞毛來源皆由陳忠露的父親逐戶蒐集而來,後來雞毛撢子生意壯大,加上養雞人家也越來越少,後來索性直接和養雞場配合,待養雞場殺完雞隻,再將新鮮的羽毛蒐集起來宅配到府,陳忠露會貼一點工錢給他們。
通常陳忠露夫婦會在清晨六點起床處理雞毛,先將雞毛泡在加了洗碗精或洗衣粉的井水洗淨。大約八、九點時,將洗淨後的雞毛均勻放在米袋上、曝曬於陽光下,靜待水分揮發之後,再依雞毛的顏色和長短來分類,方便製作雞毛撢子的時候使用。
聽到我們讚賞雞羽毛很漂亮,陳忠露突然感嘆起來:「以前的雞都是放養的,讓牠們四處跑,有運動習慣的雞,羽毛都很漂亮。哪像現在的雞都是圈養直接吃飼料,很少活動,要挑到漂亮的雞毛就比較困難。」本來只知道放山雞和飼料雞肉質有差異,沒想過連帶羽毛質感也有影響,當下也領悟難怪「飼料雞」一詞會被拿來罵人「沒用」,因為飼料雞各方面表現確實都差強人意。
為了維持雞毛撢子的品質,陳忠露尋尋覓覓合適的雞毛,果真被他尋獲以放養為主的養雞場,色澤符合陳忠露的標準,也能夠讓他們一直穩定生產雞毛撢子。「你們看,我綁的每一支雞毛撢子都很漂亮、很好用!有客人買回去也不拿來打掃,放在家裡當藝術品欣賞。」陳忠露的台語黏著海口音、也黏著自信心。
雞毛撢子製作過程需手腳靈活並用,經手超過上萬支雞毛撢子的黝黑掌心佈滿了白色的繭。陳忠露先把綿繩纏到腳拇指上頭,左手轉動木棍纏繞棉繩之際,右手則忙著挑選合適的雞毛,接著將雞毛放置於纏上木棍的棉線下,塗上白膠、拉一拉棉線便固定了。陳忠露邊塗抹白膠時邊說道:「以前還沒有南寶樹脂,都是用天然的樹膠。樹木會流出紅紅的汁,會有專職的工人去山上收下來賣我們。」
這幾個步驟反覆進行,一層又一層緩緩堆疊上去,羽毛密集地黏著木棍,垂墜的雞羽之間不留一絲縫隙。棉線切記要拉得恰到好處,才能使出力道來纏繞雞毛;同時腳還得踩著才有辦法進行,如果沒踩著距離就會不夠,連帶繩子張力也跟著不足,這樣就沒辦法綁得好。綑綁過程絕對不能心急,慢慢來比較快,纏繞得越緊,成品就越紮實耐用。陳忠露一再強調做雞毛撢子沒什麼功夫:「不要匆促,慢慢做,就會很漂亮。」
本來散落一桌的雞毛,經由陳忠露神速的「動手腳」,不用三分鐘,雞羽變鳳凰,一支華麗貴氣的雞毛撢子就此生成,猶如一場精湛的魔術表演。陳忠露台上的三分鐘,全靠台下累積的六十年功。
「雞毛撢子就跟我們人一樣,有在運動就不會壞。」陳忠露邊揮舞手中的雞毛撢子邊扭動身子說:「只要有時候拿出來動一動、偶爾曬太陽就能延長壽命,清洗的時候不要整支浸水,我的雞毛撢子可以用上二、三十年也不會壞。」我想這的確也是陳忠露長年的養身之道,養成經常運動的習慣,身體當然也就不容易生病。

一旁的許金英緊接著說:「以前嫁妝有『十二聘禮』的習俗,其中一項正是雞毛撢子。隔壁庄頭有個80幾歲的阿婆,她當年嫁人的時候,就是在我們這裡買的。之前跟她聊天,她說那支雞毛撢子到現在都還在使用。」陳忠露補充:「那一支是我老爸做的,是不是很厲害?」
我好奇問:「現在還有人遵循古禮,特別來跟你們買雞毛撢子當嫁妝嗎?」
陳忠露笑說:「現在結婚都直接寄簿子、買吸塵器啦!」
鐵棚下的牆面掛滿了毛茸茸的雞毛撢子、地面上也插著數支小巧、主攻電腦鍵盤的雞毛撢子。正常大小的雞毛撢子價格範圍落在三百至五百元,小支的則是一百到一百五元。許金英不忘說:「外頭買比較貴,來這裡找我們買會便宜一點。」
陳忠露夫婦製作的雞毛撢子,雞脖子、雞屁股、雞背、雞腹等部位羽毛皆有使用,他們信手抓來一支雞毛撢子,都能確切說出羽毛是出自公雞或母雞,以及分別是哪個部位。說到公雞的羽毛,許金英還俏皮地模仿公雞啼叫、發出「咕咕咕」的聲音;有趣的是對於雞農來說,公雞生性愛打架鬧事,又不會下蛋,標準的「生雞卵無,放雞屎有」,自然沒有生產力高的母雞受歡迎。然而在雞毛撢子市場,公雞階級大翻轉,色澤亮麗又富有彈性的公雞羽毛可是搶手貨,只要輕輕一拂,原本蒙上一層灰的地方皆煥然一新;母雞羽毛質地較為輕柔,則適合用來拂拭昂貴的瓷器或是藝術品。
陳忠露突然憶起了從前:「我小時候不聽話,我阿爸也會拿雞毛撢子揍我。」
我直笑,本來只知道臺灣雞毛撢子始祖是陳忠露的父親,沒想到早一輩流行拿雞毛撢子「教囡仔」,竟也是他帶領的風潮。
似乎是感受到我們對雞毛撢子有著濃厚興趣,不像大多數旅人僅是到此一遊,挑幾支雞毛撢子或是花十分鐘做DIY就離開。許金英示意我們稍等一下,步履蹣跚走進屋內,幾分鐘後見她手持一支套著塑膠套的長棍走向我們。隨著塑膠套褪去,原本壓抑的白色雞羽瞬間蓬鬆了起來,彷彿恢復了生命力,在陽光的加持下,更顯得雪白透徹。


整支雞毛撢子選用的白色羽毛都是出自烏骨雞,而且僅使用烏骨公雞的羽毛,因為烏骨母雞的尾椎羽毛色澤偏黃,不夠潔白。白色羽毛相對較為稀少,價格當然也不斐,一支兩千塊。
「這支買回家根本捨不得拿來打掃吧?」我忍不住發出驚嘆。
許金英解釋,通常會需要全白雞毛撢子的都是廟宇,廟方會向陳忠露訂製全長一米半的全白雞毛撢子作為驅邪法器。
雞毛撢子榮景不復返
由於雞毛撢子製作流程簡單又好上手,看著陳忠露全家總動員,街坊鄰居也紛紛投入,雞毛撢子成了時下流行的新興產業,埔鹽鄉遂成了「雞毛撢子故鄉」,還外銷到海外。曾經如廢棄物沒人要的雞毛,在他們父子倆的廢物利用之下,翻轉成臺灣之光,好不風光。
只是和眾多傳統產業一樣,一片一片依附上木棍的雞毛撢子也趕不上時代變遷的速度,各式各樣的清潔用具推陳出新,消費者對雞毛撢子的需求日漸消失,訂單被吸塵器吸得所剩無幾。雞毛撢子無法機械化大量生產,加上農村人力流失,年輕人向外尋找出路。如今,埔鹽鄉僅剩三戶人家還在生產雞毛撢子,而仍堅持純手工製作的,僅此陳忠露一家了。興許是咬牙苦撐的日子已無法在社會中存活,其他兩家採取中國預先以針線縫好的羽毛半成品,一邊快速捲動、一邊將羽片旋轉黏上已刷上白膠的木棍,技術熟練的人平均兩分鐘即可完成一支,但品質自然跟百分之百純手工的雞毛撢子相距甚遠,不只羽毛質感和美觀有明顯落差,也很容易使用沒多久就耗損。
陳忠露夫婦育有五名兒女,現在子孫滿堂,孫子多達十六名,還有兩名曾孫。我勾著陳忠露的手笑說:「阿公,那我當你第十七個孫子好不好?」沒想到陳忠露爽朗答應,還直說我就跟他的孫子差不多大。然而擁有眾多子孫的他,卻沒有一個後代,有意願繼承雞毛撢子家業。
「我跟雞毛撢子相處六十年了,我這一生只會做這個,也是我起家的意義。」
垂垂老矣的職人,看著滿牆的雞毛撢子,眼中盡是不捨,「我自己也知道這沒辦法賺什麼錢,但就是會放不下,不甘心上一代流傳下來的技術就停在我這裡。」
也許,陳忠露夫婦停止做雞毛撢子的那天,這項傳統工藝的技術,也將成為絕響,淡出在節奏過快的眾人視野。
陳忠露說,在他百年那天來臨前,還是會日復一日做下去。
「我老了啊,一塊、兩塊加減賺沒關係,我就賺老人自己要用的生活費,一天幾百塊,不用跟兒子拿錢,夠用就好了!」
常聽聞務農人家靠牛犁田賺錢,以終生不吃牛肉來表達尊重與感激。我不禁好奇,靠著雞羽撐起家的雞毛撢子職人是否也不吃雞肉呢?
許金英先是愣了一秒、隨即開懷大笑:「當然吃,我什麼都吃啦!」
雞毛撢子DIY
聽從年輕一輩的建議,陳忠露夫婦近年也開始做起雞毛撢子DIY生意,做一支簡易的雞毛撢子收費一百塊,不管人數多少,只要向陳忠露預約,他們有空的話都很樂意放下手邊事務、親自解說示範。不過,根據我們的經驗,也不用過早預約,因為第一次致電時,接電話的是許金英(依稀記得隔空都能感受到她的熱情),同行人向她預約兩週後的日子,她靦腆地表示老人家記性不太好,要我們日子快到了再打電話提醒她一下;第二次造訪,我則是前一晚打電話給陳忠露碰運氣,他同樣好客地說他隔天有在家、歡迎來作客。
「做這個賺不了什麼錢,就收個工錢,跟大家結個緣、交朋友啦!」許金英繼續說:「很多外地人都會專程來找我們學雞毛撢子,有宜蘭的、屏東的也有。」
雞毛撢子DIY體驗目前最多容納過兩台遊覽車的人數,當然田間小路連小客車行駛都有點勉強了,更何況是龐大的遊覽車?陳忠露說遊覽車會停在附近的廟宇空地,遊客再自己步行過來。趁著散步途中,望著一片綠油油的稻田、伴著徐徐涼風,也能轉換心境。
許金英得知我們特地從臺中騎了一個小時的機車前來,立即對我們比出大拇指,直誇年輕人很厲害。同時她十分好奇我們是從何得知他們的資訊:「我不識字,我先生也只有國中畢業,不像你們年輕人讀書讀很高。」然而在這裡,學歷早就不是需要被關注的重點,那份對於己業執著與鍥而不捨的精神,已然成為學校教不來、在時間長河中星光熠熠的存在了。


我本來以為DIY體驗是像他們一樣,將一片一片雞羽毛黏上木棍,但實際上是做一支小巧的雞毛撢子。因為他們發現對於從未接觸過的外行人,完成一支雞毛撢子的難度太高、大家消化不了,導致一對一教學過於耗時,老人家也顧不來。索性先將處理乾淨的雞毛縫好一串,如此一來,遊客只要先在木棍刷上一層白膠,再將一串雞毛黏上去便完工了,老人小孩也都能迅速上手,過程不消十分鐘,帶回家晾兩天後就能使用,這樣的作法也便於旅遊團能趕往下一個旅遊景點。
「前陣子兩台遊覽車的人來,我們就在庭院教大家,很快做好了。」許金英彎下腰、拿起一支迷你的雞毛撢子:「有的人不想自己做,想要直接買也可以,我就賣他一支一百,反正來這裡歡喜就好。」
此時,我的目光被掛在鐵窗的一支黑色和土黃色羽毛參半的雞毛撢子深深吸引。許金英說,黑色都是用白色羽毛去泡藥水染製而成的,工法比較麻煩一點,售價四百元。一支出自國寶級職人之手的打掃神器,一張五百紙鈔有找,還可以用上數十年,這筆交易對於消費者來說怎樣都超值。

我立即掏錢換取這支雞毛撢子的所有權。陳忠露說回家可以試著用力拔雞毛撢子,如果有掉毛的情況可以拿回來,他會直接賠一支全新的給我。唯有一心把產品做好的職人,才能對自己雙手打造出來的作品有著絕對的自信。
陳忠露凝視著一支支雞毛撢子說:「客人對我們信任,就會再來購買,我們也才有辦法生存。」
雞毛撢子團體教學
現在也有不少學校和社團單位會邀請陳忠露做雞毛撢子教學,偶爾接到來自台北的邀約,會由女兒或孫子開車載他往返,一大清晨就得從埔鹽鄉北上,進行大約三小時的課程,對於老人家無疑是一趟不輕鬆的旅程;儘管兒女已經力勸退休超過上百次,不捨年邁的父母親再那麼辛苦製作雞毛撢子,只希望他們得以含飴弄孫,安享天年;但對陳忠露而言,雞毛撢子是他這輩子的使命,能多讓一個人知道這項傳統技藝是一個;對許金英,則是能陪伴老伴做喜歡的事,多一天是一天。我問他近期還有沒有團體教學活動,他走回室內查看自己的行事曆,表示十天後會有一場,想觀摩僅存的雞毛撢子職人陳忠露示範教學的我,自然立即抓緊機會、詢問是否也能來旁觀,他豪爽地說當然沒問題。同行人建議可以與陳忠露加LINE,我正心想老年人應該不會有LINE的同時,陳忠露隨即從長褲口袋拿出手機交給我說:「給你加,阿公不會用。」縱使年近耄耋,仍走在科代尖端,步伐一點也不輸年輕人。
一週後,臺灣迎來梅雨季節,中部連日遭到暴雨的洗禮,我看著窗外的滂沱大雨,思索著雞毛撢子教學是否會如期舉行,打算晚點再致電確認。此時,手機響起LINE鈴聲,來電人是我通訊錄裡年紀最高的好友,也正是陳忠露。
「妹妹,我這裡大淹水,雞毛全部都泡水不能用了。我要跟他們約改天,你明天不要跑來。看改哪天,阿公再打電話跟你說唷!」
陳忠露至今接待慕名前來採買或DIY雞毛撢子的訪客無數,加上他年事已高,其實沒想到他會惦記著一名陌生人要去觀摩他教學的約定。
待到驟雨方歇,太陽重回崗位,我也來到教學現場。數十名學員齊聚庭院,面對一群年紀與自己兒孫差不多的人,陳忠露開場先確認:「我講台語你們聽得懂嗎?」接著拿起一隻雞毛撢子發問:「你們還有人家裡在用這個東西打掃嗎?」年紀較輕者臉上浮出斗大的問號,有名目測年約五十歲的男士幽默回應:「我小時候常被媽媽拿雞毛撢子打,現在老了看到這個還是會怕。」現場頓時一片笑聲。
簡單講解製作雞毛撢子的步驟後,便正式進入職人親自示範的重頭戲。陳忠露先用手背擦拭額頭上的汗水,接著坐在一張小板凳上,桌面備妥了所需的材料,像是雞毛、木棍、棉線以及南寶樹脂白膠。陳忠露的赤腳纏著棉線,踩在藍色夾腳拖上,拿起木棍準備大顯身手:「我先一步一步做給你們看,等一下我也會一個一個教。」

原本還在高舉雞毛當令箭嬉鬧的幾名學員,看見陳忠露展現出神入化的功夫後,無不收起笑臉、各自手持木棍忙著綑綁以及沾黏雞毛。然而雞毛撢子的製作流程看似簡單,自己實際操作,才會發現其中的難處,這項傳統技藝實則一點也不簡單。絕大多數學員都被雞毛搞得手忙腳亂,有人黏出來的成果稀稀落落、宛如一隻脫毛的雞,模樣慘不忍睹;有人的雞毛始終與棉線同棍異夢,無法相依為命;甚至有人快結束才驚覺雞毛全部都黏反了,只能從頭來過。儘管狀況百出,陳忠露仍耐心地在人群中巡視,只要看見學員有難、便一一出手相助,不僅樂於提點學員哪個步驟再加強會更好,也樂意大力稱讚學員的作品、給予滿滿的信心:「第一次做雞毛撢子就能做這樣很厲害唷!」
陳忠露不僅是國寶級的傳統技藝職人,同時也是相當稱職的活動主持人,他在活動過程還有設計有獎徵答,像是:「我手上這支雞毛撢子是用哪個部位的雞毛做的?有誰看得出來嗎?」又或是「你們知道雞毛撢子要怎麼保存,才可以像隔壁村的阿婆,一支用好幾十年都不會壞嗎?」只要答對他的問題,就能獲得小巧的雞毛撢子。問題一出,學員們紛紛舉手搶答,還有人雙手高舉、全身搖擺試圖引起陳忠露的注意,場面相當熱鬧,整堂課精彩萬分,毫無冷場。
雞毛撢子未來
雖然現代人對於雞毛撢子的需求度不如以往,但是雞羽毛含天然油脂、不會吸附灰塵,也不易起靜電,環保又耐用,對於一些家庭和愛車族來說,雞毛撢子仍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除了一般尺寸的雞毛撢子,陳忠露聽取來訪的大學生意見,也開發了符合清潔電腦鍵盤灰塵、輕巧的迷你雞毛撢子。沒想到面臨被時光淘汰的傳統清掃工具,搖身一變成為清理辦公桌的小幫手兼具療癒心靈的小物,廣受年輕族群歡迎,甚至不時還會有人專程來埔鹽鄉向他購買,當作送給親友的伴手禮,也是陳忠露始料未及的發展。
鐵棚下,可見好幾個保麗龍箱,箱子上頭標示著青森蘋果,然而許金英一掀開蓋子,不見任何來自日本的果物,反倒是放滿了陳忠露親製的雞毛毽子,一個只需一枚五十圓銅板;另一箱,則是結合雞毛的逗貓棒,滿足愛貓人士的需求。這一箱箱雞毛所衍生的產品,皆是陳忠露不安於現狀的最佳證明。一方面,他也希望雞毛能化身不同的產品,繼續陪伴著大家,只要陳忠露還在的一天,他這雙手就會持續探索雞毛運用於生活中的各種可能。


傳統技藝職人講求慢工出細活,和現代人追求方便又快速的理念背道而馳。老一輩手工職人若不懂得順應時代創新、為舊有的工藝創造新的價值,又沒有年輕人願意接下傳承大任,或是斥資轉型成觀光工廠,便只能眼睜睜倒數凋零的那一日到來。
沒有巨額資金的挹注,如何讓現代人願意放緩腳步,深入大街小巷或是鄉村聚落,認識這些飽經風霜、仍堅守信念默默於一隅耕耘的職人;如何讓品質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傳統工藝品,進而有被流傳下去的機會,顯然是臺灣不同領域的傳統產業面臨共同的難題。
我不禁感嘆,若有一天陳忠露不再繼續製作雞毛撢子,他的子孫也沒有人接續、將這項傳統文化發揚光大,是否就等同於宣告雞毛撢子正式步入歷史?一想到雞毛撢子未來有失傳的可能性,步出三合院之際,便忍不住回頭多看這座雞毛盎然的森林幾眼。
後記
雞毛撢子,是陳忠露這一生的代名詞,是讓他與許金英情牽一世的定情物,亦是開啟我深入臺灣傳統工藝領域的一支鑰匙。過去兩個月,我造訪這座雞毛撢子森林數次,不管面對的人數多寡,不論相同的往事已重複多少遍,一談起雞毛撢子,陳忠露雙眼始終閃爍著光芒,興高采烈地分享他與雞毛撢子相伴一甲子的故事。
訪談結束後,陳忠露也如關心孫子般反問我的興趣是什麼,我回答寫文章,並苦笑寫字跟做雞毛撢子一樣也賺不了什麼錢。他反倒鼓勵起我,只要是做自己喜歡又擅長的事,有耐心和決心,行行都能出狀元;於是我比先前更加積極蒐集全臺傳統技藝職人的資訊,希望自己的雙眼趕得及見證各項傳統工藝品的製作過程,單眼來得及捕捉職人們專注的身影,並透過雙手為這些國寶級人物撰寫故事,讓後人知道臺灣曾經存在過哪些無價的文化。
最近,每當寫作遇到瓶頸,抬頭看見懸掛在房間牆上黑黃參半的雞毛撢子,總會想起陳忠露說的話,「用耐心面對,用決心成功,這樣才能成事。」
本文獲得2022年磺溪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





![【小品文】人魚 [2025/9/1刊於自由副刊]](https://mywave.tw/wp-content/uploads/2025/09/20250909222900_0_fef87c-100x100.jpg)